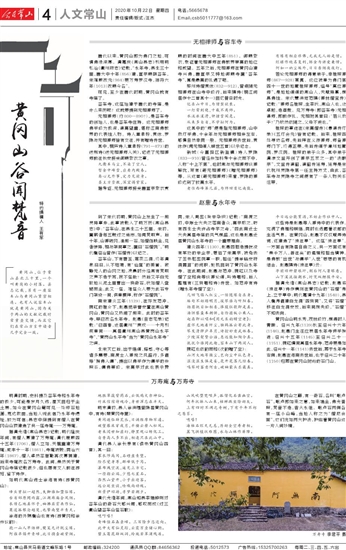黄冈山谷闻梵音
 |
| 万寿寺 李君平 摄 |
特约撰稿人 王有军
黄冈山,位于常山县北三十里,一个叫黄岗的小村落。县志记载,另有一座容车山与黄冈山紧密相连。也有人说容车山就是黄冈山,因为关于两山的文献记载时常重叠交错,而且它们在常山方言中读音几乎完全一致。
无相禅师与容车寺
唐代以来,黄冈山即为佛门之地,可谓佛缘深厚。清嘉庆《常山县志》引用明弘治《衢州府志》记载,“永年寺,县北三十里,唐大中十年(856)建,宣宗赐额容车,宋雍熙改元(984)更万寿罗汉寺,祥符六年(1013)改赐今名”。
可见,至少在唐代时期,黄冈山就有寺庙了。
容车寺,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寺庙,是什么来历呢?这就要提到无相禅师了。
无相禅师(约800—890?),是容车寺的创始人,也是容车寺住持。这无相禅师佛学修为极深,德高望重,堪称江南佛教界的代表性人物。诗人章孝标、贯休、罗隐与无相禅师皆有交往,并有赠诗传世。
其中,桐庐诗人章孝标(791—873)的送别诗《送无相禅师入关》,记述了无相禅师前往长安接受御赐紫衣之事。
九衢车马尘,不染了空人。
暂舍中峰雪,应看内殿春。
斋心无外事,定力见前身。
圣主方崇教,深宜谒紫宸。
据考证,无相禅师接受唐宣宗紫衣赏赐的时间在唐大中五年(851)。御赐紫衣,象征着无相禅师在佛教界崇高的地位和威望。五年之后,无相禅师在黄冈山建寺兴佛,唐宣宗又特地御赐寺匾“容车寺”,算是最高的礼遇了吧。
婺州诗僧贯休(832—912),曾追随无相禅师在山寺中修行,后来撰诗《桐江闲居作十二首其十一》回忆昔日时光。
忆在山中日,为僧鬓欲衰。
一灯常到晓,十载不离师。
水汲冰溪滑,钟撞雪阁危。
从来多自省,不学拟何为。
这其中的“师”便是指无相禅师,山中燃灯学佛,十余年与无相禅师相伴左右,感情自然非同一般。无相禅师去世后,贯休作《闻无相道人顺世五首》以示纪念。
新城(今富阳区新登镇)诗人罗隐(833—910)曾经参加科考十余次而不中,人称“十上不第”,他时常与无相禅师谈禅解忧,写有《寄无相禅师》《赠无相禅师》等。从这首《寄无相禅师》来看,罗隐的禅修达到了较高水平。
老住西峰第几层,为师回首忆南能。
有缘有相应非佛,无我无人始是僧。
烂椹作袍名复利,铄金为讲爱兼憎。
何如一衲尘埃外,日日香烟夜夜灯。
若论无相禅师的得意弟子,非桂琛禅师(867—928)莫属。这位被奉为佛门第四十一世的地藏桂琛禅师,谥号“真应禅师”,是地地道道的常山人,天赋异禀,颇具佛性。宋代慧洪觉范撰《禅林僧宝传》记载:“禅师名桂琛,生李氏,常山人也,幼卓越,绝酒胾。见万寿寺(即容车寺)无相律师,即前作礼。无相拊其首曰:‘若从我乎?’乃欣然依随之,父母不逆也。”
桂琛的事迹在《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皆有记载。后来,桂琛四处寻访名师,先后拜在义存禅师、师备禅师门下,终得正果,先后传道于漳州地藏院、罗汉院。桂琛的弟子众多,其中弟子清凉文益开创了禅宗五家之一的“法眼宗”,文益传德韶,德韶传延寿,延寿是宋代杭州灵隐寺第一任主持方丈,由此,容车寺与灵隐寺之间便有了一条人物关系纽带。
赵鼎与永年寺
到了宋代初期,黄冈山上发生了一起灵异事件,此事被载入了明万历《常山县志》中:“容车山,在县北二十五里。宋初,鬻薪者每五鼓过之适市,如闻梵呗声。后十年,山禅破冈,涌起一石,如僧伽趺坐,见者惊异,相与架祠事之,匾曰‘石僧院’。”明代詹绍治曾作《石僧传》以记之。
容车山,下有碧玉、莲花二洞,终年清泉汩汩,从不枯竭,有“仙窟”的美誉。寂静无人的山冈之地,凌晨时分经常有梵呗之声不绝于耳,岂不怪哉?然后又平白无故地从泥土里冒出一块奇石,状如僧人盘腿而坐,此又一怪。难怪众人要为此石专门架设一祠,供奉膜拜,称作“石僧院”。
南宋建炎三年(1129),在好友范沖、魏矼的推介下,赵鼎把亲眷安置在常山黄冈山,黄冈山又热闹了起来。此时的容车寺,早已改名永年寺。赵鼎《自志笔录》记载:“已酉春,迁居衢州”“庚戌……十月引疾奉祠……寓居衢州常山县黄岗山永平寺”,“黄岗山永平寺”当为“黄冈山永年寺”之误。
北宋灭亡后,出于悟道、释惑、守心等诸多需要,南渡士人禅悦之风盛行,多倡导“援佛入儒”,提出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儒佛兼修。宋高宗对此也表示赞同,宋人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众,高宗愍之,昉有西北士夫许占寺宇之命。”因此南迁士大夫寓居寺庙的风气颇盛,这也是赵鼎迁居黄冈山永年寺的一个重要理由。
建炎四年(1130),赵鼎因拒绝提拔没有军功的辛企宗,惹恼了宋高宗,被免去了签书枢密院事一职,担任“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的闲职,趁机回到了黄冈山永年寺。在此期间,赵鼎与范沖、魏矼以及寺僧了空和尚等谈禅论道,吟诗唱和,后人整理有《三贤唱和诗》传世。如范沖有诗《赠永年寺僧了空》:
几回飞锡入红尘,一任随缘自在身。
琢句不妨踏明月,援琴谁与听阳春。
扬眉抚目如相委,捧腹狂歌即是真。
汤饼藜羹奉朝供,自怜擔板小乘人。
赵鼎即以唱和《用元长韵赠空老》:
虚怀无地着纤尘,独鹤孤云寄此身。
琴发清弹庐阜月,诗控妙意武林春。
少陵深契赞公语,惠远能知陶令真。
扰扰今谁同此趣,容车山下两闲人。
魏矼也依韵而和《次韵赠了空》:
山河大地等微尘,岂向尘中认色身。
沤没沤生俱是妄,花开花落几经春。
鸣琴对客意何古,破袖蒙头乐最真。
平日远公能贳酒,不妨去作社中人。
这些诗是赵鼎等人禅诗中的代表作,充满了佛理和顿悟,同时也透露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在黄冈山,赵鼎不仅仅赋弄诗词,还建造了“独往亭”。这座“独往亭”, 一方面含有隐居自由之义,另一方面还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倔强和担当精神,是佛教“出世”与儒学“入世”思想的有机结合。赵鼎撰诗《独往亭》云:
亭前旧种碧琅玕,别后何人著眼看。
山下溪流接潮水,时凭双鲤报平安。
据清光绪《常山县志》记载,赵鼎将《独往亭》诗作镌刻在黄冈山的“石僧”身上,立于亭中;明代嘉靖十九年(1540),县人詹涛倡建白龙洞“四贤祠”,又将“石僧”移往白龙洞安放,后来祠废失修,“石僧”不知去向。
黄冈山山明水秀,茂林修竹,颇得时人青睐。绍兴九年(1139)秋至绍兴十六年(1146),赵鼎门生汪应辰居永年寺讲学授徒;绍兴十五年(1145)至绍兴二十一(1151),魏矼请祠寓居永年寺;范沖更是如此,绍兴十一年(1141)去世后,葬于永年寺右侧;赵鼎在海南去世后,也于绍兴二十年(1150)归葬在黄冈山附近的石门山。
万寿庵与万寿寺
明清时期,史料提及容车寺和永年寺的极少,可能是岁月久远,湮灭回归于尘土罢,如今在黄冈山麓可见一处卵石地基,宽达数亩,当地人说此信乃永年寺遗址,较为可信;县志中倒提到有僧人在黄冈山山顶建造了另一座寺庵——万寿庵。
据清光绪《常山县志》记载,明代隆庆年间,有僧人募建了万寿庵;清代康熙四十五年(1706),僧人立如、天植重建万寿庵;咸丰十一年(1861),寺庵被毁;同治六年(1867),僧人卓然率智勤再次募捐建,后来寺庵改名万寿寺。此间,虽然关于黄冈山寺庙记载很少,但也屡有文人前往游览,留下诗作。
如明代常山进士徐海有诗《游黄冈山》:
峰头曾拟一超然,失脚谁知堕俗缘。
台省郊原同雨露,江湖廊庙合风烟。
衣传乙地真怀子,袖拂层霄共作仙。
莫道孤根沦越楚,也擎南壁半青天。
徐海的外甥詹山也有诗《游黄冈和徐参议韵》:
抱一山人早悟禅,樊笼无计脱尘缘。
阿谁卓锡开青嶂,此日携壶破紫烟。
地胜草蔬皆药石,云低鸡犬亦神仙。
竹床信宿诗魂冷,身世浑忘在半天。
明末清初,县人徐洪瑆曾隐居黄冈山中,有诗《题黄冈寺壁》:
黄冈避俗辟荒丛,日诵维摩物罕通。
破壁藤床穿夜月,半楼云磬入松风。
老来阅世知虚幻,静里观心转化工。
自昔高人多不出,相逢只在此山中。
清代县人徐长泰有《读书黄冈山四首》,其一曰:
搴衣陟高冈,石磴盘青壁。
险尽觉身尊,群峰低于舄。
瀑布溅空流,遥见上方宅。
一径指云端,少憩七星石。
岿然山堂开,小子出迎客。
远公延坐谈,崄巇尚动魄。
新景俨旧游,寻梦若朝夕。
清代光绪年间,常山知县李瑞钟则对容车山的奇石大感兴趣,感叹而成《过三衢山望容车山怪石歌》:
噫吁嘻!
奇峰怪石森叠嶂。三百馀步恣还向。
此中大有仙灵踪,云霞万叠储心胸。
碧玉莲花辟双洞,玲珑岩翠滴残冻。
山风吹堕梵呗声,孤僧化石凿幽空。
何年托钵入山来,枯禅跌坐馀劫灰。
上有四时不凋之奇树,下有千年不朽之苍苔。
噫嘻!
海枯石烂天无恙,历劫全空寿者相。
翼飞拱植状难图,永与山林作屏障。
在黄冈山之巅,有一奇石,名叫“毗卢石”,毗卢即如来之意,如来端坐,佛光普照,梵音不绝,香火永继。毗卢石两侧各有一座小山峰,当地人称之为“僧尼会面”,它们犹如两大护法,护佑着黄冈山这一片人间妙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