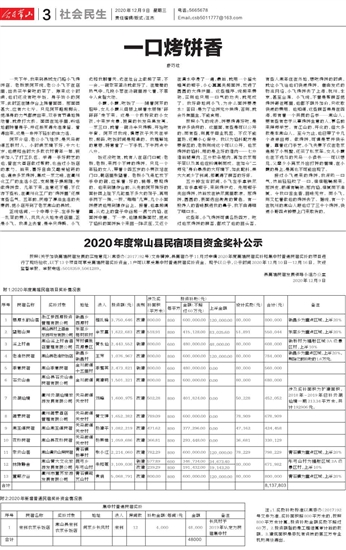一口烤饼香
舒巧壮
一天下午,我来到县城龙门路小飞烤饼店。老板娘阿芬说,老公小飞不在店里,出去买午餐吃的菜了。原来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吃午饭。身子娇小的阿芬,此时正在操作台上揉着面团。那面团甚大,应有六七斤。只见阿芬踮起脚尖,把浑身的力气都使出来,双手有节律地揉动着,就像打太极。面团在她手里,听话地翻转着身子,并逐渐变得光洁滑溜。看得出来,这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体力活。
阿芬介绍,老公小飞姓缪,是天马街道五联村人。小时候家境不好,十六七岁,他便和当时大多数农村青年一样,辍学加入了打工队伍。学得一手好厨艺的他,曾在大酒店做过帮厨,也当过小饭店的掌勺。后来,喜好自由又酷爱钻研的他,遍尝多家烤饼,集成一家之味,在衢州化工厂的生活小区,支起棚子摆起摊,专做烤饼卖。几年下来,生意还不错,不仅存下些钱,在衢州化工厂的“烤饼圈”还颇有些名气。五年前,厌倦了漂泊生活的夫妻俩,把小店开到了老家常山的县城。
正说话间,一个中等个子、左手拎着一扎菜的男人,风风火火地走进店里,正是小飞。我凑上去看,是半只烤鸭。小飞边和我聊着天,边在灶台上做起了菜,不一会,一碗紫菜蛋汤就做好了。在腾腾的热气中,几段小葱在汤碗里游弋着,不禁令人食指大动。
小霞,小霞,吃饭了……随着阿芬的招呼,女儿小霞从阁楼上顺着木楼梯“砰砰砰”走下来。这是一个极标致的小女孩,十来岁光景,披肩的长发乌黑发亮。一家三口,就着一碗汤半只烤鸭,开始吃午餐。阿芬对我说,情愿孩子天天在学校,起码,吃饭时间是规律的。我理解她的意思,特意看了一下手机,下午两点十八分。
饭还没吃饱,就有人在店门口喊:老板,老板,来两个不辣的烤饼。只见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站在门口,朝店里张望着。老板小飞连忙放下手中的碗,应承着:好的,稍等,要现烤的。他来到操作台前,从先前阿芬揉好的面粉团上扯下几砣差不多大的剂子,再用手两下一揉,一按,“啪啪”几声,几个小面饼便被他甩到操作台上。接着,他拿起调羹,从边上的盘子中舀起一满勺肉馅,往面饼中塞。下一步,他操起擀面杖,把包了馅料的面饼挨个来回一阵滚压,又逐个在清水中浸了一遍,最后,就用一个溜光锃亮的钳子,小心翼翼夹起面饼,放进了圆圆的大烤炉里。这些程序,说起来费劲,实则他只用一口气的功夫,就完成了。我好奇地问小飞,为什么面饼要浸水?答曰:是为了让饼充分烘烤,否则,就会外焦里生,不能食用。
按照小飞的说法,饼要烤得好吃,是有许多诀窍的。这里面,有些是可以公开的;而有些,则属于商业机密。不仅不能宣扬,还需小心保守。我以为馅料配方是要保密的,老板则说这个可以公开。他家烤饼的馅料,用的是上好的猪肉——七分猪后腿瘦肉、三分肋条肥肉,再加农家梅干菜以及其他佐料调制而成。在如今“二师兄”身价暴涨的大环境下,如此配料,虽大大减少了利润,却赢得了顾客的好评。
五分钟左右时间,小飞左手拿铁笊篱,右手拿钳子,来到烤炉边。先用钳子夹出烤饼,然后放在铁笊篱里歇凉。那烤饼,圆圆的,表面透出微微的黄色。有一股馋人的香味飘进我的鼻子,我不由得咽了咽口水。
这些年,小飞烤饼可谓名扬四方。吃过他家烤饼的顾客,都成了他的回头客。有些人常年住在外地,想吃烤饼的时候,就让小飞给他们快递烤饼。借由发达的物流网络,小飞烤饼去了上海、杭州、北京,甚至台湾。小飞说,不管是帮顾客把烤饼寄往哪里,他都不额外加价,只收取快递的费用。他知道,这些顾客虽身在四海,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常山人。更有些有志于从事烤饼生意的人,慕名前来拜师学艺。有江山的、开化的,但大多数是本常山人。至今为止,他已带了十几个徒弟出师。做烤饼,可谓是累并快乐着。靠着这门手艺,小飞夫妻不仅在老家造起了小别墅,还买了私家车,女儿小霞也在不远处的天马一小读书……可以想见,父辈少小离家外出打拼的窘境,在小霞的身上,是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接过小飞递来的烤饼,我深吸一口气,然后轻轻咬了一口,细细咀嚼起来。那饼皮,筋道有嚼劲;那肉馅,细腻而不油腻。令我口舌生香,回味无穷。而小飞,则又忙着做他的烤饼去了。据说,有一个在杭州的常山人跟他订了三十个烤饼,快递小哥四点钟要上门来取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