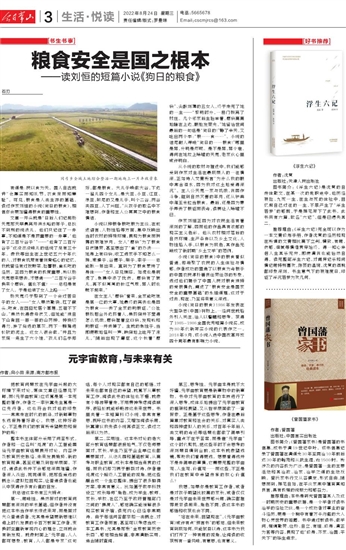粮食安全是国之根本
——读刘恒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
 |
| 同弓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一期地块上一片丰收景象 |
石刃
有道是:民以食为天。国人自古就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廉耻”。可见,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读过作家刘恒的小说《狗日的粮食》,相信你会更加懂得粮食的重要性。
文章一开头就是“日后人们记起杨天宽那天早晨离开洪水峪的样子,总找不到别的说法儿。他们只记住了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顶重要的一件事。‘他背了二百斤谷子’”——“他背了二百斤谷子”这没滋没味儿的话说了足有三十年。像我等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对粮食饥荒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就曾经有过挖野菜、捡薯根、偷瓜吃的经历。正因为粮食的极度重要,所以杨天宽思来想去,才想通——“二百斤谷子换来个瘿袋。值也不值?……总归是有了女人。于是他领了女人上路……”
杨天宽终于娶到了一个会过苦日子的女人——“女人果然勤快,扛了镢头、吃食,在囫囵坨搭个草棚,五宿不下山。”虽然长得像母夜叉,但她能“独自下山背回一篓一篓的山药种。种块切得匀,拌了烧透的草灰,两下一颗掩进松软的泥土。这女人很会做。”并且为家庭一连生了六个娃,“孩儿们名字却好,都是粮食。大儿子唤做大谷,下边一溜儿四个女儿,是大豆、小豆、红豆、绿豆,煞尾的又是儿子,叫个二谷,两谷夹四豆,人丁兴旺。”从孩子的取名中不难想到,作者和主人公冥冥之中的粮食情结。
小说以种粮争粮吃粮为主线,在叙述语言、人物性格等方面,集中反映出当时农村的特殊环境,展现为粮食而拼搏的艰难岁月。女人“瘿袋”为了粮食日夜操劳,甚至想出了“偷”的办法——她身上有口袋,收工进家手不知怎么一揉,嫩棒子、谷穗子、梨子、李子……总能揪一样出来。直到为了粮食累垮了身体——“女人日见憔悴。如虎也是病虎了,急躁中添了忧伤。瘿袋有了皱儿,再不似亮亮的粉红气球,骂人时也鼓不起来。”
在女主人“瘿袋”看来,全家能吃饱是第一位的大事,她最终的离去也是因为粮食——丢了全家的购粮证。“公社粮栈柜台外边挤着人,虽挤倒并不显得怎么饥饿,瘿袋捏着空口袋,发现钱和购粮证一并丢掉了。生就的急性子,当即便嗷地怪叫一声,跌倒地上吐开了沫儿。”随后出现了癔症,这个长着“瘿袋”、尖酸刻薄的丑女人,终于走完了她的一生——“黎明时分,一扇门板离了村庄。几个邻家后生抬举着,瘿袋高高地睡在上边,眼脸发荣光,”她留给世间最后的一句话是“狗日的!”静了半天,又吐出两个字:“粮……食……”。小说的结尾耐人寻味“狗日的……粮食!”哪里是骂,分明是疼呢。是不是骂,骂个谁,得问在她坟上唏嘘的天宽,老家伙心里或许明白。
从小说的取材与描述中,我们能感受到作家对生活在最底层人的一往情深,正如诗人艾青所言“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主人公天宽一家与饥饿、贫困作斗争,碰到自然灾害的年月,还从驴粪中淘玉米粒当粮食。最后,还是因为妻子弄丢了粮证而丧命,读罢让人唏嘘不已。
作家刘恒正因为对农民生活有着深刻的了解,因而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他从农村相对落后的自然环境、生产条件以及乡土文化、人物性格入手,以粮食为底色,其作品无疑成了新时期“乡土文学”的范例。
小说《狗日的粮食》中的粮食看似普通,却凝聚了农民的人生体验与情感,作者成功的塑造了以粮食为命根子的中国农民淳朴善良任劳任怨的形象,透过他们揭示了中国人民对粮食独特的爱恨情仇,阐述了“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的永恒道理,这对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意义深远。
小说《狗日的粮食》1986年发表在大型杂志《中国》刊物上,一经问世就格外引人关注,给人以警醒和思考。获得了1985-1986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8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之一。2018年9月,该小说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