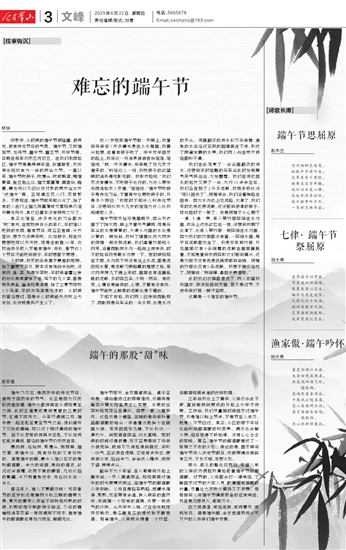端午的那股“甜”味
郑忠信
端午乃双五,是阴历中的传统节日,有别于阳历中的节气。也正是因为双历的阴差阳错,端午大都游离在小满和夏至之间,此时正值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时节,忙得不可开交。今年巧遇闰二月,端午便一路狂彪至夏至节气之后,貌似避开了双抢的高峰,可以过个相对清闲的端午节。但不论怎样的游离与狂彪,不论如何忙乱与清闲,曾经的端午节仍历历在目。
裹肉粽,烙烧饼,蒸馒头,剥蒜瓣,插艾草,绑端午线,既有好玩的又有好吃的。酒是端午的甜,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吃甜酒酿。半大的瓷碗,微白的酒液,欲沉还浮酒糟,浓而不腻的醇香,几近沦陷的瓢羹,千万别着急动手,先让口水流一会儿。
曾经年少,谁人不慕甜滋味?无奈春节的压岁钱还是嫌两分钱三颗的糖果太贵,夏天的青枣从来留不到转色成熟的时候,秋野的桔子贼酸柿子超涩,冬日的糖锤和油茶花蜜一样可遇而不可求,惟有端午的甜酒酿总是如约而至,鲜甜无比。
端午节那天,全家围桌而坐。桌子正中是一道白里透红的蒜瓣猪肉,外围则是腌菜炒黄瓜和盐渍空心菜梗。水嫩的空菜叶和苋菜各自清炒。四素一荤,众星拱月。这些只是个铺垫,压轴的是母亲拎着盛甜酒酿的钵头一手拿着汤匙挨个往碗里分装。来来回回好几趟,不论长幼,一律均分。刹那酒香四溢,口水直咽。那时候的时间过得很慢,好不容易等到了母亲分装完毕,就迫不及待地凑向碗边,深吸一口气,正欲狼吞虎咽,忽觉有点失态,便佯装淡定,轻舀半勺,徐徐送入嘴中,闭而不语,频频点头。
韶华不为少年留,自从哥哥到外地上高中后,一家人围桌而坐、和和美美过端午的时光便嘎然而止,但端午节的甜酒酿从未中断。父母自是轻车熟路,把糯米淘净、蒸熟,放至带有余温,拌入研碎的曲药中,中间掏一个可爱的酒窝,外蒙一块透气的纱布。头天中午入钵,次日中午就可开怀畅饮,是名副其实的速成版家酿美酒。每逢端午,父亲就会提着一个竹篮,将甜酒和美食准时送到校园。
三年后我也上了高中,父亲仍乐此不疲,直到哥俩到更远的外地上大学才作罢。工作后,我们尽量抽时间回家过端午节,只是难以踩上节点,不是节至人未齐,就是人齐节已过。其实,小区的楼下平日也能听到甜酒酿的叫卖声。偶尔也会解个馋,但总觉得不够地道。没有心心念念的那味。莫名,端午节的甜酒酿竟成了一抹挥之不去的乡愁。幸运的是,国家早将端午节纳入法定节假日,放假带调休起码有三天,不长不短,足慰乡愁。
而今,做儿的鬓也已斑白,年届八旬的父亲依然满腔热情地做着端午节的甜酒酿。过节前,父母都会打一道电话,了解回家过节的大致人员,酌情增减酒酿的份量,尽量让大家吃个痛快又不浪费。每每接到父母端午节请假报备的征询电话,我自是沉思良久,感慨万千。
古之把酒者,或话桑麻,或问青天,或祝东风。酒是端午甜,余亦把酒恭祝千家万户的父母亲们端午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