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端午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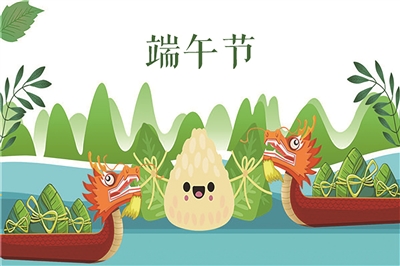 |
林华
小时候清明过后,就掐着手指头盼望端午节的到来。因为家里穷,平时别说吃肉,就连粗茶淡饭也常常吃不上,而那时候越穷越能吃,因为肚子里没油水,只要能吃的都吃得有滋有味。我10来岁的时候一顿可吃几碗番薯丝拌的饭,可常常在盛第二碗时就会听到大人不寻常的咳嗽声,那是无言的警告,其意是“小孩子有一碗还不够,还要盛第二碗?”几次后我自然心知肚明,于是每餐只吃一碗,胆悸去盛第二碗,除非趁大人不在时才急速地再盛一饭勺。
印象中,以前很难吃到白米饭,大多是番薯丝干拌米饭,即使这样,仍常常饔飧不继。唯有过节的时候,才有米饭吃,并能闻到些许荤味,哪怕一家人就半斤肉,也多少能解点馋。所以,那时候小孩盼着过节,大人却怕过节。
我10岁那年端午节的前几天,母亲独自一人时就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可在我们姐弟面前又强装笑容,若无其事似的。我不知何故,就悄悄问姐姐,姐姐比我大几岁,比我懂事许多,她说:“可能是因端午节要到了,母亲因没钱买肉和没有糯米包粽子而发愁吧。”我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去跟母亲说说,我们不吃肉也不吃粽子,只要母亲开心就好。姐姐说:“你真傻,端午节是传统节日,有钱人没钱人都得过,岂需我们瞎操心?”什么叫传统节日,我当时不懂,我只知最好有肉吃,有粽子吃,实在没有,不吃也没关系。
端午节的前两天,我和姐姐放学回家,看到母亲将一点糯米浸到水里,我猜想,肯定是包粽子的,想起过年才吃过粽子,那箬叶散发的清香,那甜而不腻的味道,至今仍记忆犹新。只要想起吃粽子,喉咙里就情不自禁地吞几下。
傍晚和姐姐去采猪草时,我对姐姐说:“端午节还是有粽子吃的,母亲将糯米都浸下去了。”姐姐说:“就一升半糯米,还是母亲跑了好几家才借来的。”我不知姐姐为何知道这么多,看她每天也是上学,回家后我们一起采猪草或砍柴,怎么我不知道的事她却知道。
端午节那天,恰逢是星期天,早上起来,母亲将一大盆热乎乎的粽子放在桌子上,叫我们姐弟先吃。我迫不及待地剥开一只粽子咬一口,真是好吃极了。尤其那一小条肉,吃在嘴里爽滑酥嫩,回味悠长,我舍不得马上吞下,让它在嘴里多停留一会,让味蕾多享受一会,直到它即将溶化再吞下。
吃了两个粽子后,觉得余味正浓。正想去拿第三个的时候,姐姐突然眄睨我一眼,我赶紧将伸出的手缩回来,顿时大悟,因为还有父母、外祖父和外祖母等几个人没吃,我一个小鬼若要吃3个粽子,真是“超量”了。但我猜想,粽子肯定还有的,不会就这么几个。
临近中午时,我和姐姐各挑着一担柴禾回家了。刚放下柴禾时,看见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年乞丐到我家里,左手拄着根拐杖,脏兮兮的右手端着一只脏兮兮的碗。母亲正好从厨房将一碗苋菜端到堂前桌上,看着乞丐的碗,又看了看桌上剩下的2个粽子,迟疑片刻后,拿起一个粽子放在乞丐的碗里。乞丐边说着多谢的话,边往门外走去,“等一等。”母亲边说边端起苋菜走向前去,朝乞丐碗里添了些苋菜。乞丐又说着多谢之类的话。这一幕正好被我看在眼里,开始我觉得母亲太大方,早知这样,我早上多吃一个粽子也无妨。可当我看到这老年乞丐步履蹒跚,孤苦伶仃的样子,我很快为刚才的想法感到羞耻,而另一种想法跃进脑海:“早知这样,我早上宁愿少吃一个粽子给这位老爷爷多好。”
中午时分,母亲和往年端午节一样,拿着个畚斗,将石灰撒到屋里的每个角落,并边撒边口中念念有词:“杀什么?杀毒虫,杀什么?杀蛇杀蜈蚣。”我不知其意,又悄悄问姐姐,姐姐说:“农村习俗,端午节正午在各旮旯里撒了石灰,就不会有毒蛇、蜈蚣之类的害虫到家里来了。”我若有所思后说:“那去年夏天曾的一条蛇跑到家里来,难道去年端午节母亲没有撤石灰吗?”姐姐说:“每年都撒的,也许,如果不撒的话还不止一条蛇到家里来呢。”
傍晚时姐姐还告诉我,就我们姐弟吃的粽子里有肉,母亲他们吃的粽子里面的馅是咸菜。我听后不禁泫然,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心想,母亲她们实在不容易。
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虽然家里很穷,但端午节吃粽子、饮雄黄酒、给小孩涂雄黄、悬挂菖蒲、艾草、佩香囊、给小孩缠七彩线等习俗始终没有改变。
回忆往事,无疑会枨触万端。倘若说给小孩听,他们会说我是天方夜谭,或者怀疑我是否脑子有问题。
